202361读书笔记|《我与地坛(插图版)》——有些事只适合收藏,不能说,也不能想,却又不能忘
202361读书笔记|《我与地坛(插图版)》——有些事只适合收藏,不能说,也不能想,却又不能忘
作者史铁生,是散文+诗歌的一本书,散文居多,最开始看完了诗歌,不是很惊艳,前边的散文我看的很慢,很细致,15万字看了10个多小时,1个月将近的时间,断断续续看完。
他的文字是有力量的,情感是丰盈的,有些话语也很有哲理,仿佛承接着过去,又承载着未来。透过他的文字,看一些人的故事,经历。仿佛是个冷静的旁观者,又带着温热的温度在看待,属于他人的人生与经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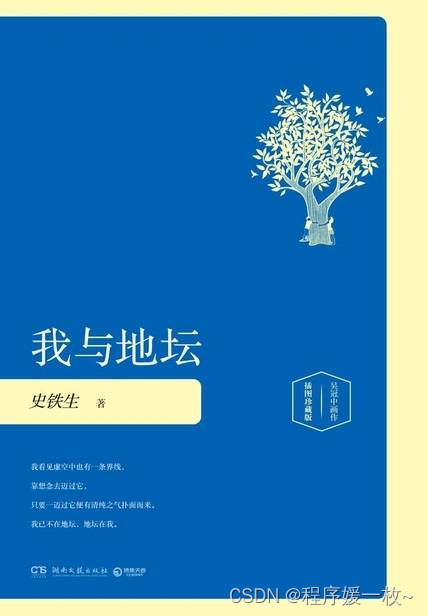
部分节选如下:
-
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,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,并看见自己的身影。
-
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,还来不及为母亲想,他被命运击昏了头,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,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。
-
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文思枯竭,那样你就又完了。
-
活着不是为了写作,而写作是为了活着。
-
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。
-
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。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。
-
我什么也没忘,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。不能说,也不能想,却又不能忘。
-
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,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,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:心与坟墓。
有些心情无人可说
有些过往只适合珍藏只要你知道它存在过
其实就够了有一段时间觉得
一些事情有点不够
可慢慢想
发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😘😘 -
我忽然觉得,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。
-
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,时而悲怆时而欢快,时而缠绵时而苍凉,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,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,响在现在,响在未来,回旋飘转亘古不散。
-
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,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。
-
但是太阳,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。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,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。
-
黄色的花淡雅,白色的花高洁,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,泼泼洒洒,秋风中正开得烂漫。
-
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,我闭上眼睛,想: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?迷迷糊糊地,我听见回答:“她心里太苦了。上帝看她受不住了,就召她回去。”我的心得到一点儿安慰,睁开眼睛,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。
-
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。悲伤也成享受。
-
上帝为了锤炼生命,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。
-
在科学的迷茫之处,在命运的混沌之点,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。不管我们信仰什么,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。
-
“忘我”未必都是好事,有时竟是生命的衰竭和绝望。
-
惭愧常使人健忘,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,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。
-
记忆的筛眼里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,还容易走进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。
-
自己为自己盖棺论定是件滑稽的事,历史总归要由后人去评说。
-
它们所以没有随风刮走,那是因为一辈辈人都从中听见自己的心,乃至自己的命。
-
现在是将来的过去,现在是过去的将来,将来是将来的现在。
-
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。你能知道你现在正走向什么?你能知道什么命运正向你走来吗?
-
被你洗掉了的种种排列,未及存在就已消逝,上帝只取其中一种与你遭遇。
-
母亲对未来的祈祷,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,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。那时我开始写作,开始恋爱,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。可是合欢树长大了,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,几年后我的恋人也远去他乡,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。然后我的妻子来了,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,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。
-
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,落满细碎的枣花。
-
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,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,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。
-
钟声沉稳、悠扬、飘飘荡荡,连接起晚霞与初月,扩展到天的深处,或地的尽头……
-
这颤抖是一种诉说,如同一个寓言可以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,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。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,譬如夜的流动,毫不停歇。这颤抖,随时间之流拓开一个孩子混沌的心灵,连接起别人的故事,缠绕进丰富的历史,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。恐怕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记住她。未来,在很多令人颤抖的命运旁边,她的影像总是出现,仿佛由众多无声的灵魂所凝聚,由所有被湮灭的心愿所举荐。于是那纤细的手指历经沧桑总在我的发间穿插、颤动,问我这世间的故事都是什么,故事里面都有谁?
-
我双腿瘫痪后悄悄地学写作,母亲知道了,跟我说,她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写作。这样说时,我见她脸上的笑与姥姥当年的一模一样,也是那样惭愧地张望四周,看窗上的夕阳,看院中的老海棠树。但老海棠树已经枯死,枝干上爬满豆蔓,开着单薄的豆花。
-
拒马河上绿柳如烟,雾霭飘荡,未来就藏在那一片浩渺的苍茫中……我循着母亲出嫁的路,走出院子,走向河岸,拒马河悲喜不惊,必像四十多年前一样,翻动着浪花,平稳浩荡奔其前程……
-
想:那顶花轿顺着这河岸走,锣鼓声渐渐远了,唢呐声或许伴母亲一路,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她是怎样的心情?一个人,离开故土,离开童年和少年的梦境,大约都是一样——就像我去串联、去插队的时候一样,顾不上别的,单被前途的神秘所吸引,在那神秘中描画幸福与浪漫……
-
母亲对父亲的缺乏浪漫常常哭笑不得,甚至叹气连声,但这个男人的诚实、厚道,让她信赖终生。
-
在它飘逝多年之后,在梦中,我常常又听见它,听见它的飘忽与悠扬,看见那摇铃老人沉着的步伐,在他一无改变的面容中惊醒。那铃声中是否早已埋藏下未来,早已知道了以后的事情呢?
-
我仿佛又听见了那钟声,那歌唱,脚踩落叶的轻响,以及风过树林那一片辽阔的沙沙声……
-
记忆,所以是一个牢笼。印象是牢笼以外的天空。
-
窗外是无边的暗夜,是恍惚的晴空
-
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,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。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,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——“真的,你一定行”——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。
-
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,在雨雪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,爱恋,因其暂时而更珍贵。
-
群山响彻疯狂的摇滚,春风中遍布沙哑的歌喉。
-
春风强劲也是一座牢笼,一副枷锁,一处炼狱,一条命定的路途。
-
盼望与祈祷。彷徨与等待。以至漫漫长夏,如火如荼。
-
秋风起时,疯狂的摇滚才能聚敛成爱的语言。
-
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,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,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:心与坟墓。
-
强大的本能,天赋的才华,旺盛的精力,张狂的欲望和意志,都不得不放弃了以往的自负,以往的自负顷刻间都有了疑问。心魂从而凸显出来。
-
呢喃的絮语代替了疯狂的摇滚,流浪的人从哪儿出发又回到了哪儿。
-
披一身秋风,走向原野,看稻谷金黄,听熟透的果实砰然落地,闻浩瀚的葵林掀动起浪浪香风。
-
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。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。
-
写,真是个办法,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。
-
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,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,写作之终于的寻求,即灵魂最初的眺望。
-
可你看地坛,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,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,五百年,安静了;安静得草木葳蕤,生气盎然。
本文来自互联网用户投稿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不代表本站立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 如若内容造成侵权/违法违规/事实不符,请联系我的编程经验分享网邮箱:chenni525@qq.com进行投诉反馈,一经查实,立即删除!
- Python教程
- 深入理解 MySQL 中的 HAVING 关键字和聚合函数
- Qt之QChar编码(1)
- MyBatis入门基础篇
- 用Python脚本实现FFmpeg批量转换
- spring 项目配置中一些问题和使用方法
- 【CUDA】五、基础概念:Coalescing合并用于内存优化
- RS232、RS485、RS422、CAN、USB
- 【【迭代16次的CORDIC算法-verilog实现】】
- 分数1/1-1/2+1/3-1/4+1/5 …… + 1/99 - 1/100 求和
- MySQL面向对象回顾3
- 4.14 构建onnx结构模型-Min
- 龙年新春礼物:智能教育产品成家长新宠
- 医院信息系统集成平台—数据交换层
- ubuntu卸载dock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