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49读书笔记|《陈年喜的诗》——杏花岁岁结出青杏 岁月是永恒的 善变的是人类的命运
《陈年喜的诗》作者矿工诗人陈年喜,今年还读了一本外卖诗人的《赶时间的人》,也很惊喜。脚下是泥泞的土地,心中是灿烂的繁星。我喜欢生活与生命的厚重烙刻在他们心灵的痕迹,有心酸艰苦,但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,向上的力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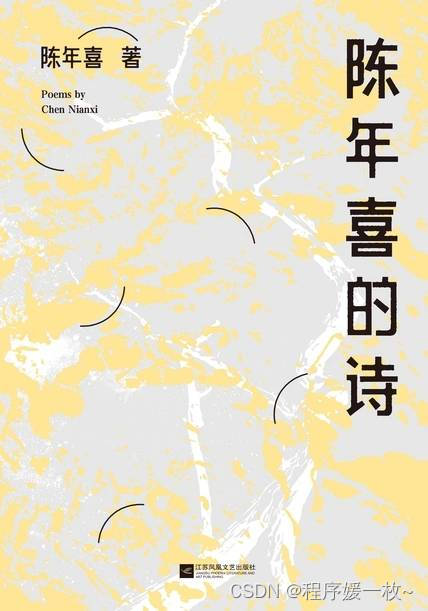
部分节选如下:
-
这些年身如飘蓬 除了一盏灯 一场大雪 只有诗歌把我接纳
-
从本质上说,所有的诗歌都是挽歌,挽长天落日,也挽孤夜寒声,挽大江大河,也挽每一株小草,挽青春、生死、无尽的时间。
-
浓密叶片的深处 我看见过一颗 深秋里唯一的 黄澄澄的果实
-
人一辈子 像马一样急促 但谁也走不到路的尽头 谁也不能从一条路走到另一条路上
-
我曾长久注视过一株稻穗 注视过它的沉重和轻盈 在太阳落下的黄昏 它们大面积说话 那无边无际的语言被蛙声听懂
-
朝霞中的它们 还有核桃树的叶子被镀上了一层共同的光晕 峡河在山下静静流淌
-
天黑了 街头的灯光依次亮起来 照彻这座巨大的城市 初秋的风吹亮什刹海的波涛 也吹动玄武门上远去的钟声
-
世上的路并不都通向远方 时钟的飞速转动 也是另一种彷徨
-
一树合欢照江流 照一个人一生少有的悲伤 它是汹涌的 有波涛的苍黄
-
命运一直是这样 翻过一座山 还有一座山 通往山顶的路逼仄 陡峭 飘摇 蜿蜒 苦楝子开满路途 唯有合欢越来越少
-
多少年里对着那些卑微的 沉重的物事和命运 她总是先轻轻地吹一口 然后用尽一生的力气接住
-
岁月是永恒的 善变的是人类的命运
-
世界的变化云翻雨覆 而内心的更易何其缓慢
-
其实人的奔波不过是黑发追赶白发的过程 我们想想有什么不是徒劳呢 作为徒劳者 奔跑在徒劳的事物之间 努力而认真
-
我们对于爱情的理解总是过于繁复 除了锦开花簇还有细细地 缝补
-
人类的智慧让离别更加便捷 快速黄昏即将降临 阳光铺满了广场 我突然没有了悲伤 只有感动 在一个火车开动的下午 让我看见了告别以及告别的轻重
-
杏花岁岁结出青杏
-
相对于遥远的过往 我更爱河上黄昏的汽笛 它拖动长长的水流 也拖动沿岸将熟的黄橙
-
羊群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红柳要到秋天才红 红柳招揽北风是葡萄下架后的事情 在海拔最低的吐鲁番盆地 没有传奇 无草而肥的羊群是最大的奇迹
-
二〇〇六年夏天 一群人翻越天山 天山阔大无边 以一群羊做背景 羊群是流动的 但比天山还沉默 火车是跑动的 一群人比火车还要沉默 羊群的沉默多么饱满 我们的沉默早已空空荡荡
-
时间一直这样把一只果子变腐 把一个早晨迁徙到另一个暮境
-
把吹过的风 把经过的死再经历一次 同样需要伟大的勇气
-
人间所有的思念总是慢于植物的速度和尺度
-
历史和爱情总是延续惊人的相似 传说有新奇但从未有过新意
-
山桃花沉默 用骨朵说出内心的矜持
-
我看见漫山的花木 要么未开要么已经开尽 只有大云寺孤零零站立在兜头大雨中
-
历史轻薄 谁没干过献媚的勾当 时间的宽容在于 从不秋后算账
-
山河与建筑 有什么秘密可言 无非是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无非是旧痕再覆新苔 地理的每一次洗牌都是落日的局 唯有大雨不容篡改
-
赤红的山脊拒绝落日的和解 寸草不生是它的使命
-
时间就是这样能让朱颜改 也能让铁树枝头年年开出无改的繁花
-
一只蝴蝶从镜框里飞过 又在一丛苦楝子花上落下 仿佛那句无法猜透的谶语
-
多少年来 我们对地理的理解一直停留于山水 其实山水并无新意 比如盘锦有什么能比落在其上的一场大雪更有意思呢 它落在百尺高楼 也落在穷人的院子 使一条大河的美德在大雪之下重被提起 而一群麻雀借一片背阴的雪地绘画出万物共同的晚景
-
动车追逐着Wi-Fi 将时间送向一个更加破碎的远方
-
所有的生者与死者拥风而眠 如一树玉兰叶的阴面与阳面
-
花春巷桃花初开 新春无涯 诗意与浪漫填满了季节不多的空间
-
地里的玉米已经怀穗 它安静的长势让万物羞愧使我深信 所有的黄金都不能让它转过身子
-
比起热闹的世界 他们更爱白纸上的清贫
-
她们的疲倦与遗忘 正好配得上这长途漫漫的夜晚 成为世界最后的诗篇
-
所有的命运 总是呈现出与追赶相反的镜像
-
父亲一些时候愿意抱起你 放在疲惫的肩头或者膝上这时候 他把世间的所有都放下了 他变得很轻 多少事物可有可无 任迎面的生活翻山越岭
-
一棵树与另一棵互相倚靠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成为亲人 一些时光接过一些时光 一些死亡落在一些死亡上 我爱这绵亘的漫长
-
战争的烽烟何曾消弭 死亡与生存争夺着同一片高地
-
文字建构的世界日益晦涩屑碎 唯自然保持原始的力量与气象
-
暮晚 山雨初霁 月亮像一朵杜鹃开在秦岭西峰
-
在一个只生长风景的地方 贫穷总是唯一且低调的
-
在抵达尽头之前 像音符逃出响器 完成一次失败的转头
-
古老的黄河静静流淌 十里槐林甘芬荡漾 黄花犬善解天意 露星星的帐篷就是故乡
-
渐老的人在墙角独自打旽 白露已过 一场秋雨一场寒 月季繁艳 在风中飘落 落在身上的几瓣将他残破的梦抚慰
-
苦楝树显得更加高大 夜间雪为它长出了新的叶子
-
喧嚣的日月在山脚的大河上亡命流淌
本文来自互联网用户投稿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不代表本站立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 如若内容造成侵权/违法违规/事实不符,请联系我的编程经验分享网邮箱:chenni525@qq.com进行投诉反馈,一经查实,立即删除!
- Python教程
- 深入理解 MySQL 中的 HAVING 关键字和聚合函数
- Qt之QChar编码(1)
- MyBatis入门基础篇
- 用Python脚本实现FFmpeg批量转换
- java练习题之继承(创建对象时属性先赋值输出再执行构造方法)
- strict-origin-when-cross-origin
- 基于java的企业合同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
- mysql之四大引擎、账号管理以及建库
- 【算法】代码随想录刷题记录 | 4. 字符串篇(含KMP算法详细步骤及代码)
- Excel小技能:excel如何将数字20231211转化成指定日期格式2023/12/11
- 邮件服务支持Exchange协议,资产历史账号支持设置保留数量,JumpServer堡垒机v3.10.2 LTS版本发布
- 目标检测入门体验,技术选型,加载数据集、构建机器学习模型、训练并评估
- 【JavaSE】Java入门七(抽象类和接口详解)
- 第11章 GUI Page423~424 步骤六 支持文字,使用菜单,对话框输入文字